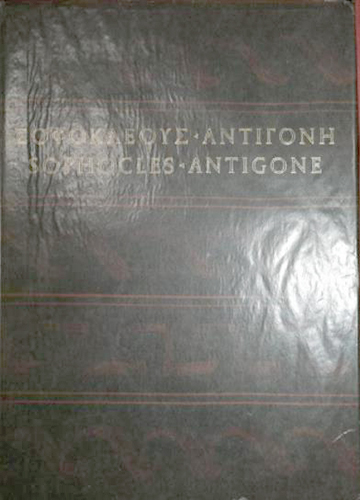
《安提戈涅》是埃斯库罗斯最著名的戏剧之一,约于公元前441年成功上演,赢得极高的荣誉。这是一部引起诸多争议的悲剧作品,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城邦法治与宗教神律孰高孰低,国家秩序与人性孰褒孰贬。从表面上看,索福克勒斯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安提戈涅尽古老宗教的义务和家庭责任,为手足之情而死,其行为可歌可泣,是无可厚非的。克瑞翁作为一国之主,维持社会秩序,打击叛军,维护法律的尊严,实行法治,也是无可厚非的。从另一角度看,安提戈涅偷葬行为违反国法,有碍社会秩序;克瑞翁禁葬违反神律,漠视人间情感,两者都有过错。那么,诗人所要褒扬的正义在何处?也许只有回到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才能理解索福克勒斯的心灵。
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正逢雅典民主政治全盛时期,当时社会的风尚是倡导民主精神,反对僭主制度。所谓僭主即指那些利用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趁机夺取政权,实行专制统治的人。索福克勒斯对僭主深恶痛绝,他曾说:“谁要是进了君王(指僭主)的宫殿,谁就会成为奴隶。”《安提戈涅》被认为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风尚和诗人情感的剧作。剧中人物克瑞翁是僭主的典型写照。他口口声声说要使人民安乐,实际上是将人民视为奴隶,“人们必须对他事事顺从,不管事情大小,公正不公正”。正如歌队长所指责的,“(克瑞翁)有权力用任何法令来约束死者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把城邦的法令摆在神律之上,专制而无情,一定要置安提戈涅于死地,让波吕涅刻斯死无葬身之地。当时的希腊社会,仍有氏族社会的宗教遗风,认为神律是不能违反的,当人世间的法律和宗教神律相抵触时,必须放弃法律。克瑞翁的禁令触犯了神律,会殃及人民,他的口头法令根本不能成为国法,他仍一意孤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众叛亲离。诗人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对安提戈涅的遭遇深表同情,高度赞扬她勇敢和顽强的精神,借歌队长的话说,“这个女儿天性倔强,是倔强的父亲所生;她不知道向灾难低头”,“她是神,是神所生;我们却是人,是人所生。好在你死后,人们会说你生前和死时都与天神同命,那也是莫大的光荣!”当守兵发现安提戈涅为波吕涅刻斯举行葬礼仪式时,没有按照克瑞翁的禁令,用乱石砸死,而是将她捉起来,表明守兵在心里仍然同情安提戈涅的遭遇。在第三场中,克瑞翁的儿子海蒙不畏父亲的淫威与之争辩,说全体市民都认为安提戈涅是“做了最光荣的事,在所有的女人中,只有她最不应当这样最悲惨地死去!”海蒙指责克瑞翁是在进行专制统治,最好“独自在沙漠中做个好国王”,因为“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这些细节的刻画,都表明诗人褒扬的是安提戈涅的牺牲精神,反对冷酷的专制统治。
《安提戈涅》全剧共分七场,本书选取第二场安提戈涅受审、第三场海蒙与克瑞翁的争辩和第四场安提戈涅对人生的感叹这三个著名的场面进行赏析。索福克勒斯是写人的能手,他善于塑造人物形象,三言两语便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美学效果。他尤其喜欢采用对照手法,在相互比照中凸显人物的个性。比如第二场中,诗人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安排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一审一答的过程,在互动中彰显人物的个性,使人物的性格成为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样,第三场中,诗人引出海蒙这个角色,观众在克瑞翁与海蒙的争吵中进一步了解剧情和人物。儿子海蒙的个性与父亲克瑞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重了戏剧冲突。索福克勒斯的语言风格质朴简洁,富于联想,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剧中有很多巧妙的答辩和诡辩的言语。从安提戈涅受审和海蒙争辩这些精彩情节的对话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索福克勒斯戏剧的语言之妙。
夏陌2023-01-04
分类

微信公众号

文学联盟
(微信扫码)